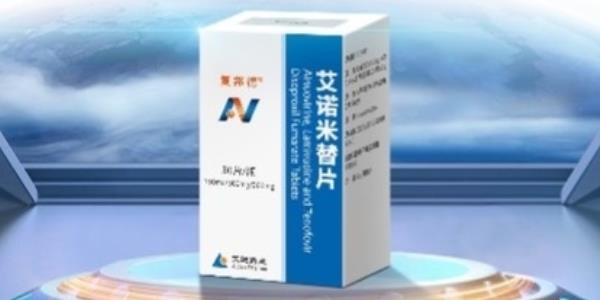西安艾滋病患者的隐匿人生
艾滋病来源:西部网2015-06-17
公开数据显示,从1992年陕西省发现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2014年10月底,陕西省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携带者累计达5885人。在西安市定点收治艾滋病人的第八医院,从2010年到2015年,接受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的人数从76人猛增到2100多人。他们的年龄、身份各不同,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竭力将自己隐匿起来,害怕自己的病情被人知道。
怕泄露隐私,催生代领药服务
6月4日一大早,西安市第八医院二楼西南角的性病科里陆续赶来一些领取免费药物的年轻人。与西安其他医院到处排队的情况不同,在这家以治疗传染病为特色的医院里,整个门诊部相对有些冷清。穿梭其间的是一位穿藏蓝条纹T恤、皮肤黝黑的瘦高个儿,40岁上下,他一见到新面孔便上前询问:“确诊多久了?给你一张名片。”
名片上简单地印着一个名字:张欣,后附电话和QQ号码。名片的背面则印着代领药品、艾滋病毒检测、心理开导等服务。接到名片的人通常不愿多聊,张欣会主动介绍自己:“我确诊都5年了,只要坚持吃药,身体好好的。”
发完名片,张欣又回到科室外大厅的长凳上,一边“刷”手机,一边朝楼道口张望,时不时地还用手压一压身旁鼓鼓的单肩包。包里放着的是他刚从该医院领出的几盒抗病毒药物和检测试剂。他在等待自己的老客户——一名要他帮忙代领药品的艾滋病人。而这种称为“鸡尾酒疗法”的药物是医院免费发放的,可有效控制感染者体内的艾滋病毒。
最近几个月,张欣明显忙了许多。医院方说由于药品厂家供应不足,将本应每次发放3个月的药量改为每次只发一个月的药量。因此,来医院领药的病人比往常多得多。2100多个病人等着领药、做各项检查、开处方,性病科里的4个大夫和3个护士忙得团团转。
按照规定,每个在医院建档的病人都需本人亲自来领药,但有时病人会因故无法定期来医院,考虑到艾滋病人一旦停药,病毒的耐药性便大大增加的风险,在与医生协商后,往往能获得些许照顾。张欣提供的“VIP”服务便是这种政策“人性化”的产物——帮一部分病人代领药品。每一次将这些药品顺利地交到对方手上,他便能拿到30元的跑腿钱。
对于自己的“客户”数量,张欣不愿透露。因为相似的经历,他明白要他帮忙的人都各有各的难处。收费低廉,守信用,日子长了,与他合作的老客户又介绍了新的客户给他。QQ群里的400多人加上手机通讯录里的100多个病友,都是他潜在的服务对象。
对于病人的情况,张欣也从不多问。但他知道“来这吃药的啥人都有,有大学老师,还有的自己就是干医疗行业的。”张欣见过开豪华越野车来取药的中年男人,也有搭出租车来的病人家属,取完药还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曲江买貂皮大衣”。
一个让张欣代领药的女病友让他印象深刻:“我俩说到××医院的大夫,她都认识,她不敢来领药,说都是一个系统的,怕被人知道,还问我该咋给老公说,害怕传染给对方。”“还有一个大学老师,和我交了朋友,有不便给人说的都找我倾诉。还请我去他家,他是我见过的‘男同’里为数不多的和家庭关系和谐的,老婆也知道他的病。但不敢给家人说实话,只能说是找异性时感染的。”
第二次见到张欣是一周以后。他向记者透露:“除了名片上的服务,还可以帮着抽血化验。”见记者不信,他解释,“其实很简单么,就是把客户本人的血抽了,再找人拿着身份证去疾控检查。疾控上确诊是要身份证的,反正保证血是他的就行了呗。其实也没啥么,可他们就是不愿上医院来。”
艾滋病房里最缺的是临床陪护
11日上午,在西安市第八医院性病科的诊室里,一名领药的病人让医生靳娟感到无奈,“4个月的药你吃了半年,明显是服药依存性不好。还有,上次给开的检验单也没有做。”这是一名有着吸毒史的艾滋病人,他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吸毒被抓进戒毒所待了两个月,耽搁了领药。
靳娟向病人解释:“艾滋病的传染途径就像乙肝一样属于慢性病,发现早,早干预服药,艾滋病人的寿命与正常人几乎没差别。不怕你服药晚一点,就怕依从性不好。吃着吃着停了,很容易导致病毒耐药性。”
曾经专修过心理咨询师的靳娟认为,导致病人私自停药的因素很复杂,“有出差或因故没有带够药的,家人又不知情或不方便来医院,还有的没啥感觉就停药了,也有的认为得这个病就是个死,没信心吃药。”
服药依从性不好、失访或私自停药的严重后果,恐怕没有人比八院住院部艾滋病房的临床陪护心歌更清楚。去年,是他亲手将两名被家属遗弃的艾滋病人遗体送到了太平间。
去年大年初一凌晨5点,时任西安市第八医院艾滋病科住院部主任李飞宇接到科室电话,来自延安的病人郑某的家属跑了。李飞宇急得心里发毛,没想到第二天却听到一个让人欣慰的消息,病房里一个叫心歌的义工愿意无偿照顾老人。在后来的工作中,李飞宇见到心歌为70多岁的病人郑某理发、喂饭、翻身,非常专业,便开始向其他病人家属推荐心歌。病人郑某在住院治疗一个多月后离世,期间除了“心歌”和医护人员,没有再见过一位亲属。去世前几日,奄奄一息的郑某用微弱的声音对心歌说:“非亲非故,你把我感动了,谢谢。”心歌记得,当晚送老人到太平间后,他和李飞宇都没有说话,可两人都流泪了。李飞宇说:“艾滋病人的晚年是最可怜的。”而心歌则从老人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晚景,“我老了估计也是这个下场。”
其实,40岁的心歌也是一名确诊多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男同”加上艾滋病人的身份逼得他在老家渭南无颜立足。2010年,安顿好老小之后,他跪在地上磕了响头,从此漂在西安,断了回家的念想。
“临床陪护在艾滋病房是最缺的,大夫亲自去请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干,不管你给多少钱,听到这三个字都直摆手。别说陪护,就连有的家属来了都不愿靠近。”6月11日上午,已调任该院重症监护室(ICU)主任的李飞宇医生告诉记者,“有的感染者发现得晚,还有的与疾控部门失访了,或者自己停药了,等到发生机会性感染才送到医院来,再合并其他肿瘤和脏器病变,几乎都是危重病人。”
出于对病友群体命运的关注,心歌与几位病友几年前创立了艾滋病病友互助小组“博爱家园”,为住院艾滋病人提供陪护等。心歌说,他想为感染者建立一个“中途之家”,为受到歧视的感染者提供一个心理开导、关爱救助的安全港。然而,由于收入微薄、身份敏感,目前几乎找不到愿意长期服务的志愿者。此外由于未在民政部门注册,“博爱家园”暂时还无法向外界申请捐助。心歌说,有好几次自己差点改行去当保安,好歹生活有保障。
李飞宇认为:“陪护对于艾滋病人尤其重要,一个因素是照顾得好就恢复得快,另一个因素是心理支持。被亲属遗弃、歧视,很多病人精神先垮了,而这些工作仅凭医院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如果不是在“性病科”里遇到来取药的安可,没人会把艾滋病和眼前这个精力充沛的男孩联系起来。1991年出生于西安周边农村的他,上初二时父亲去世,19岁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这两件事让他在一夜之间长大。安可还记得上高中时班主任得知他是同性恋时的反应,“啥?啥叫个GAY?”当他在纸上写下“同性恋”几个字时,那个自诩“活了40多年了啥没见过”的老师傻傻地愣了好久。
高中时“出柜”表明男同身份、17岁出现高危性行为并感染、19岁确诊。随后便失访、发病,再治疗。安可的经历可以说是如今诸多年轻感染者的缩影。为了不被家人和同事发现他艾滋病人的身份,安可4年没回过家。期间做过很多工作,从酒吧的服务生到售楼部顾问,再到企业白领。
2014年,被调往上海的他因感冒发展为肺积水,他发着高烧连夜坐动车回到西安八院住院。哥哥来看过一次后便不再来。安可一个人在医院昏昏沉沉地躺了十几天,总算捡回一条命。有了这次经历,安可每到新单位上班前,都会提前给主管打招呼:“我可以周末加班,但我有事的时候你必须让我休假。”因为担心被领导知道,住了院也不敢报销,更不敢让同事知道自己在“传染病医院”领药。
安可说,他最痛心的就是看到青少年走自己的老路。“以前我看电视上播艾滋病的新闻,只说河南农村卖血会感染艾滋,然后很快就会死亡,可在那之前,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同性恋也会感染。”
如今的安可是艾滋病感染者组织“爱之家”的志愿者。经过治疗,他在生理指标上已经不算是艾滋病患者了。他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告诉更多的年轻人艾滋病是什么,如何保护自己。
然而,根据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信息,在我国,只有50%的人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也就是说,就算让所有知道自己患病的人接受治疗,也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治疗。一份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调查显示,目前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只普及了中国20%到40%的高风险群体。西安市疾控中心性病与艾滋病科科长卫晓丽告诉记者:“性教育我们近几年一直在大力去做,每年在多所西安高校都有关于性教育的科普活动。”但另一个尴尬的现状是,在中学阶段推广性教育难度要大得多,“疾控中心去联系学校,上课要占用时间,很多学校都不愿配合,大多数学校更关心学生的考试成绩。可青春期是性安全教育的关键时期,等上大学了再去讲,青春期早过了。国外的性教育从上幼儿园就开始了。”
在南郊某小区的“爱之家”,记者看到许多二十出头的年轻面孔。他们既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服务该群体的志愿者,有西安某大学的学生、银行职员、政府公务员,还有医生以及被男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同妻。
来自湖南的志愿者“小倩”说,“我感染的时候怕得要死,不敢给任何人说,遗书都写了,可是觉得死后被人家知道又很丢人。我就在网上发帖子,没想到好几个外地的网友打来电话鼓励我,说这个病可以控制、不要怕等。那是我活了二十岁第一次觉得心里那么温暖。所以现在看到有人得艾滋,我一定会去关心他、鼓励他。”
“爱之家”组织负责人吴勇透露,目前工作的重心是病友关爱和维权。吴勇将自己的电话放到网上后,每周都会接到多个艾滋病人因手术被医院拒绝的求助电话,“爱之家”便出面与医院交涉。另一个让志愿者们激动的好消息是,去年以来,在“爱之家”的成员中,已经有10个病友家庭经过药物干预和阻断生下了健康的婴儿。
“谁让你们这些人好好的搞什么同性恋?”曾有医生不止一次地这样问过吴勇,他会告诉对方另一种逻辑:“那些没有卖淫、嫖娼、吸毒的人也会得艾滋,同性恋的妻子也是无辜的感染者。他们‘洁身自好’了,却还是被感染,问题出在哪里?”
“在西方国家,早在20年前艾滋病就已经是重要的公共健康议题,但在中国,与性有关的话题都是隐晦的,可如果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保护自己?”吴勇说。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 香港男男感染艾滋病创新高 最小10岁
2015-02-25
- 共享修指甲工具 英国一女子感染艾滋病
2014-11-14
- 香港首季新增84名同志感染艾滋病个案
2014-05-28
- HIV新病毒株 艾滋病患者更快发病
2013-12-02
- “禁艾入浴”将会加重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2013-10-21
- 适度运动可改善艾滋病患者脑功能
2013-08-21
 精彩推荐
精彩推荐
-
- 国产三合一艾滋病新药艾诺米替片(复邦德)
-
艾滋病 2023-01-18
-
- 不戴套的经历!60%的GAY半年内无套过
-
艾滋病 2022-11-05
-
- 帅哥被HIV感染者恶意传播 暴露后紧急阻断
-
艾滋病 2022-08-11
-
- 什么是pep暴露后预防?高危后艾滋病阻断!
-
艾滋病 2021-11-07
-
- 艾滋病!怎样会被感染?怎样不会感染?
-
艾滋病 2021-09-20
-
- 国产抗艾滋病长效注射剂艾可宁(艾博卫泰)
-
艾滋病 2021-09-18